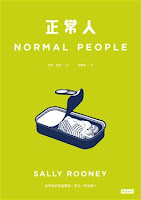|
| 《海上鋼琴師》劇照 |
那麼多城市,根本讓人看不到盡頭,盡頭在哪裡?拜託,能讓我知道哪裡才是盡頭嗎?
當時我站在舷梯向外看,覺得一切都棒。穿著那件駝毛大衣,感覺充滿自信,我準備好下船了。說真的,那並不是問題。
不是我看到的東西阻止我,麥克斯。而是我看不見的東西。你懂嗎?是那些我無法看見的。偌大的城市,綿延無盡,但卻沒有盡頭。根本沒有盡頭。我看不見的,正是一切結束的地方,是這個世界的盡頭。(It wasn't what I saw that stopped me, Max. It was what I didn't see. Can you understand that? What I didn't see. In all that sprawling city, there was everything except an end. There was everything. But there wasn't an end. What I couldn't see was where all that came to an end. The end of the world. )
拿鋼琴來比喻吧,鍵盤有始,也有終,88個鍵就在那裡,這錯不了;它並不是無限的,但音樂卻是無限的。我能在有限琴鍵上演奏出無限的音樂。我喜歡這樣,我也應付得來(I like that. That I can live by. )。
但當走過舷梯之後,前面會有……人生成千上萬的琴鍵,那是真實且沒有盡頭的,麥克斯。那個鍵盤是無限大的。當琴鍵無限大,就無法在那鍵盤上演奏出音樂;那不是給凡人彈奏的,那是屬於上帝的鋼琴(But if that keyboard is infinite there's no music you can play. You're sitting on the wrong bench. That's God's piano.)。
老天啊,你看過那些街道嗎?僅僅街道就成千上萬條!一旦上了岸你又該如何選擇?去愛一個女人,去住一間房子,去挑選一塊可以讓你擁有自己風景的土地,最後挑一種死去的方法。整個世界讓你喘不過去,你甚至不知何時才會結束,何處才是盡頭,太多的選擇怎不讓人精神崩潰,怎能讓人活得下去。
我出生在這艘船上,與這世界擦身而過。每回上船的僅有兩千人,不過這裡充滿了希望,但這夢想僅存於船的船尾之間。(I was born on this ship. The world passed me by, but two thousand people at a time. And there were wishes here, but never more than could fit on a ship, between prow and stern. )
用有限的琴鍵奏出自己的幸福,這就是我學會的生活之道。
陸地,對我而言,是艘太過龐大的船,是個太漂亮的女子,是條太漫長的旅程,是瓶太濃烈的香水,是篇我無從彈奏的樂章(It's music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我永遠無法捨棄這艘船,我寧可捨棄自己的生命,反正對世人而言我不存在。除了你,麥克斯。你是唯一知道我在這裡的人,但畢竟你是少數,你最好習慣這樣。朋友,原諒我,我是不會下船的。
***
 |
| 《海上鋼琴師》劇照 |
突然明白,自己這種人,終其一生只會適合一件事。如此可能的幸福,只發生於一方天地,其範圍剛好讓路過的人駐足,並能憑藉那樣擦身的時間,交付眼前心底的音樂,流連及其心底。
成就是屬於可被多數人轉述的故事;但說真的,不是不在乎,我只是無從想像。更願在茫茫人海中有一個專屬的席次;我可以,我也喜歡,那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