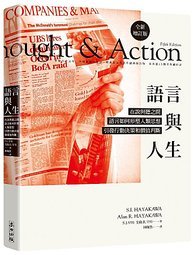不樂意內嵌文青覺醒的文創周邊(讓觀者自我感覺良好的「媒體素養」贖罪券,有看有保庇?),僅存連結為證:
用新聞台打口水戰! 老闆最愛自媒體♥ 【記者真心話】 Vol.5
方姓主持人自己搶先站上一個道德制高點,假中立又師心自用,別人遂都是白痴了。
從前,我們學古典新聞總說閱聽人平均程度為國二。但這條懶人包型雞湯影片(將問題簡化再簡化)大概認定電視新聞的觀眾都是小二生。
若依方先生的跳接邏輯(鄉民做夢式)照樣照句,《紐時》、CNN天天罵川普挺拜登,肯定是財團老闆的手伸進去,將媒體當作自己的粉專,美國記者終究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嗯?)。
(題外話:您自己能不能先定義什麼是「自媒體」?那您這個頻道算不算公視的自媒體?以及,到底這個牆國營銷術語為什麼能在各種實務界如此無入而不自得啊?)
今夕何夕,從數位喊到後數位的網路昌明年代,竟還有人懷舊地秉持「電波頻譜稀有論」觀點,加以認定「廣電媒體」基於公共利益而只好(/能)中立分配各方勢力嗎?是否請身為同輩的您環顧一下具體的現實脈絡,此時此刻,大家(/您本人)主要的新聞資訊取得是電視新聞嗎?電視新聞的影響力還真是眾人幻想得那般永恆巨大嗎?那其他「平面/電子媒體」算不算新聞來源,他們要如何分配或歸納勢力範圍?前幾日臉書河道上一片數位哀悼日本男星三浦春馬的聲量難道是來自電視新聞嗎?
(一覺醒來回到上世紀)
上世紀的理論要不要更新?今日的媒體環境需不需要好好校準認知一番?
眼下,您還在嘴電視新聞。豈不比長輩還要lag,他們都在用LINE分享來路不明的假新聞了呢。
承您思路斷言,「廣電新聞」(雞婆地幫地圖炮的你畫箭靶範圍好了)癥結點是財團,然後症狀是政治立場,所以藍綠各打五十大板,最終指向唯有中立才有真正的自由。(這邏輯套接大家都覺得順理成章?)
所以,地球上哪一個國家的新聞媒體沒有「政治勢力」(其定義範疇為何)涉入?您是否稍微讀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文獻(爬梳各國歷史脈絡,分述諸如西歐、南歐、美國、日本、南韓等不同淵源情狀的傳媒與政商關係)?
主打實務經驗而要您靜下心來讀書,太難了嗎?那我們討論職業倫理。
最讓筆者詫異的,莫過於您含沙射影地指控個別新聞工作者的「guts」(切莫同您批判的主流媒體躲在引述網友的說法後以卸責)。您已可證實主播張雅琴受電視台老闆指示不去報導某事件了?出家尚可還俗,惟您主張,新聞工作者不能生涯轉向從政?甚至,您認為新聞工作者不該也不能同時加入個別政黨(新聞自由高過個人自由——《憲法》第十四條結社自由,敢係按呢)?
再回頭思考您的影片訴求。私以為,問題在於,您企圖探討結構問題,卻錯誤而廉價地操作起名人的名利風波,射箭畫靶——這種流量蹭法,十足小報格調。
(無所謂事實關聯的真確)帽子扣好扣滿,口氣益發堂皇岸然;內容無非陳腔,腳本一逕操作膝跳反應,渾然忘我地演示電視感官主義——這副老成油氣面孔(責難口吻,凜然姿態,曉以大義的情調)似曾相似,正是周楚除害那樣自婊了,唯獨扮小清新入魔的您顯然病識感闕如。到底就是一個販賣自我感覺良好的人,連自己都騙了。
其中的立論前提實是各種站不住腳,筆者就只揀一點批,有立場根本不是問題。您「直覺」(學院中人卻與公園裡下棋阿伯異口同聲!反正就是「為富不仁」不是嗎?)以為媒體老闆賺錢是靠立場/選邊站?恰恰相反——當下,做新聞沒立場(即您最愛的「中立」)儼然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環節,正所謂「和氣生財」,一如美聯社[註1]那樣的上游資訊機構,追求意識形態的真空(這當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就是了),裨益廣泛而毫無顧忌地兜售各方人馬[註2]。然,真正落實言論自由的媒體環境難道不是各擁所宗/各說各話,方能互相制衡與監督——「真理/真話」才有辨明的機會,一派「和諧」又何庸對話?就實務的經驗論,沒有立場就沒有觀點;沒有觀點無非只是佯裝討論/表演對話的形式,除卻某種自我感覺良好(常見兩(多)面並陳的呈現/模樣,比方請反同人士來「有話好說」,真是一個台性)其實毫無意義(您總得衡量價值高低,揀擇一個方案、傾向一個更正義或至少正確的立場來處事/世吧)。
假立場說嘴,不過行草船借箭之實——藉著陣營之間的宿讎來為自己的正當性打雞血,以回頭攻擊線上的工作者——這種無聊激憤而不知所云的過敏反應,委實文青。
至於如此不齒財團,身為一個認真「左派」(抑或此詞如今已費解地由范氏一幫(編譯系)國際新聞狂粉透過超譯混淆等同為「自由派」?),為了面對開門就燒錢的電視台錢坑,您就應該古典地倡議向台灣民眾收取月費或年費來辦一家台版BBC(值得一提的是,政大修習通傳法課上,前大法官之子、法律系教授曾言,公視今天這種素質他繳不出來),祝福您。
認真希望您能在台大新聞所花些時間讀書,而不是花人民納稅錢在公視當網紅。
P.S 看到同溫層轉傳這部影片,真是可悲。大概這個圈子的人彼此都認識,根本不容許誰講一些真話(誠哉他結語「包含對你不利的真話」,至於「說真話」到底跟「愛台灣」又怎麼牽上因果關係我也毫無頭緒(順藤摸瓜整部腳本就是莫名其妙的邏輯硬扣到底到讓人放棄思考。。。
[註2] 客觀、中立作為一種原則,起因於「好賣」,用來對記者的報導進行規範與檢視,使報業經營者不用擔心趕跑讀者,同時也討好廣告主。(關於這種「中立內容」的極致,眾人可以想想所謂的三機/器新聞,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街口監視器,是哪一家台灣電視台的心頭好,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