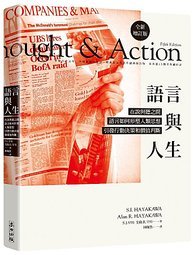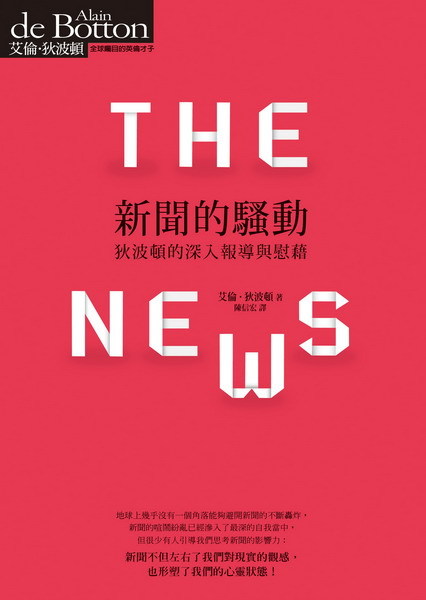
不同於我在學院派的學習經驗,動輒以內部組織(權力、倫理)、外部結構(政經、文化)分析,左批判右套牢,談著談著,千絲萬縷而又身陷泥淖,仰天長歎,疲憊者敗下陣來,新到者接棒戮力。我們,重複地,不曾間斷地,呼籲並修正一紙記載迢遠而可能的處方箋(寫作、剪輯、編製),同占星那般觀看與紀錄著,探詢摸索的過程很多發現與感觸,但最終,仍然留下無法真正企及的惋息。
這本書分章立節地探討起當今新聞困境──國際新聞,乏人問津的曲高和寡;災難新聞,不忍卒睹的殘忍血腥;名人新聞,膚淺俗濫的八卦小說。若同從前,我們誠然可以一路審問下去,傳喚閱聽人、傳媒、記者等人出庭(例如靠北記者這個粉絲專頁),並藉由各方證據的拼湊,疊合起一絲一線瑣碎細微的徵象,仔細檢調整條產製過程中的各個環節,指認出各種名狀下的框架理論肇生的鏈鎖式症狀;但最終,如同我們帶著伴其一身的慢性病進到大醫院,掛哪一科都有所缺失,吃哪一顆藥丸都有副作用──儘管,某些時候,某些階段,體膚心理之痛楚能夠獲得某種程度的紓解,但我們仍得小心翼翼地維繫著這一點靈光,視其為偶發的幸運,無比珍惜,不至於天真到以為能夠阻擋「壞下去」的時間之輪。
然而,我們相信人生並非如此,我們一定能夠突破現狀。
這不啻是
- 談面對政治帶來的失望,常常只是毫無來由的樂觀所致。
「新聞拒絕接受人性現實,於是任由希望一在沖刷在同樣的淺灘上。新聞裝出一副天真無邪的姿態迎接每一天,卻總是到了傍晚就不免對我們的處境充滿盛怒與幻滅。……。實際上,我們就許多面向而言仍是個無可救藥的物種──這點並非偶然,而是根本上就是如此;此外,我們在關鍵時刻也不該氣急敗壞,而應當保持深沉平靜的憂鬱心態。」(P.65、66) - 談陳腔濫調下的同一化困境,泰半是我們誤信並縱容笨蛋的自以為是。
「現代的笨蛋能夠輕易知曉過去只有天賦異稟的人士才可能知道的事情,但儘管如此,這麼一個人卻仍然是個笨蛋──過去的時代從來不必擔心這種令人沮喪的組合。」(P.81) - 談產製國際新聞需運用「細節得以連結建立起相對的切膚感」的藝術原理。
「把焦點投注在這些平凡元素上並不會削減『嚴肅』新聞的力量,反倒是能夠提供一座穩固的基石,讓我們對駭人及干擾正常生活的事件能夠產生真正的關切。」(P.97) - 談財經新聞的疏離感受,如同夜半一再侵擾的荒涼叩問。
「……;另一方面,我們卻也懷有許多粗淺、天真、單純、熱切又強烈的渴望,又總是刻意將這些渴望隱藏起來,也通常不願提及,只怕一旦表露這種盼望,將不免有失體面及成熟嚴肅的姿態。」(P.150) - 談名人新聞帶來的閱聽人效果:嫉妒,是我們習焉忽略的負面影響。
「當然,嫉妒的效用有其限制。過度提醒別人的成功,可能只會使我們陷入恐慌與麻木,並且無意間導致我們無法將任何計畫付諸實行。我們聽到別人達成種種工業的消息,不免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壓力。我們必須不讓自己的內心與外界隔絕,處於平靜的狀態,才有可能完成有價值的事物:也就是有一天可能引起別人嫉妒的事物。」(P.191) - 談災難新聞的悲劇深意,得以作為寓言啟示,協助我們度過人生裡的變數。
「新聞中大部分的內容,終究乃是陳述世界各地的人,在各式各樣的立場中犯下嚴重的錯誤。這些人沒有能夠在還有時間的情況下掌握自己的情緒、節制自己的執迷、判斷是非對錯,以及作出適當的行為。我們不該虛擲從這些人的失敗中獲取教訓的機會。……,藉此讓我們在安全的狀態下,已充分的餘裕發展出最好的因應方式。」(P.222) - 談意外報導裡「虛空」的雙面角色,藉其平衡生活裡各種的拉鋸折衝。
「死亡的念頭能夠讓我們看待事物的先後順序而獲重新安排,撥開日常生活中的煩擾,而使自我當中較有價值的部分再度浮現出來。看見人生中真正值得害怕的事物,能夠在驚恐之餘,致力追求內心知道自己應當追求的人生。」(P.227)
「我們都太習於把感同身受與人性畫上等號,以致遺忘了偶爾保持麻木也是一種必要的成就。……,那些問題畢竟不總是屬於我們的問題。」(P.231)
以上。回歸真實世界(實務或學術),我們心知肚明這些闡述很難成為